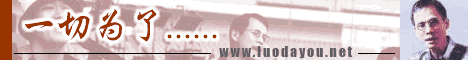
为周杰伦入选爱国歌曲鼓掌 2005年03月16日 新京报
哼哼唧唧的周杰伦,虽然人们并不在乎他究竟口齿不清地得吧了些啥,却也总是津津乐道他唱的那些歌词。但那些古堡荒原半兽人,只是粗糙的象征主义加上无意识的意识流拼凑,类似于采样拼贴,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忽然平地一声惊雷,闻得周杰伦的一首《蜗牛》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之列,同时被收入的还有《真心英雄》、《中国人》等多首流行歌曲,不仅鼓掌叫好,也不得不哑然失笑。
听着一个在各种场合吝啬笑容、衣着破烂得考究、眼神迷离得高科技的歌坛小天王,和着动听的旋律清唱“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就算没有人推荐,也根本不会妨碍孩子们随之神魂颠倒,想象自己与偶像一起在精美MTV中化身超级蜗牛,肩负各种版本的美梦,与各种现实的boss争斗,而且正义与胜利当然属于坚持不懈的我方。这一切看上去再正常不过。
有趣之处在于,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这还是第一次,上海市科教党委有关负责人称,民族精神教育决不是说教,要适应儿童少年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而且这次向中学生推荐的100首歌曲主要还是学生喜欢唱的,至于周杰伦的《蜗牛》,入选原因主要是“思想内容十分上进,唱起来琅琅上口”。这不能不让人鼓掌叫好,因为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泛滥的各种流行文化向来是学校严防死守的洪水猛兽,此次既然可以选取一些真正处于流行音乐漩涡中心地带、拥有既成事实霸主地位的歌曲,正大光明地鼓励学生们传唱,了解比不了解强,疏导比围追堵截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鼓励可以成为拥有家长话语权的一方正视青年流行文化存在的一次契机,为更广泛地理解、尊重、鼓励多元化的青年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另一方面,令人哑然失笑的原因则在于,且不说“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的提法是否不大合适的问题,单说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本身,是否又意味着一种不符合青年文化规律的选择呢?好比市面上王二麻子家的糖炒栗子好吃,或者不好吃但吃糖炒栗子正时髦,男女老少早就用嘴和钱包投了票,如果贴出一告示,曰王二麻子家的糖炒栗子味道不错向18岁以下馋嘴孩童严重推荐云云,颇有多此一举之嫌,这还不算张三家孩子与李四家孩子虽然都馋嘴,但可能张三家孩子好甜中带咸,李四家孩子好咸中带甜这种复杂情况。
还有,新问题也冒出来啦。周杰伦不过是一首《蜗牛》入选,按照逻辑这首《蜗牛》必然生存于一堆其他歌曲的CD之中,倘若其他歌曲歌颂情情爱爱的不符合推荐要求,难道要《蜗牛》单独发行一个“爱国主义歌曲推荐”单曲珍藏版?
本报文娱评论员 江海蓝
为周杰伦入选爱国歌曲鼓掌 2005年03月16日 新京报
哼哼唧唧的周杰伦,虽然人们并不在乎他究竟口齿不清地得吧了些啥,却也总是津津乐道他唱的那些歌词。但那些古堡荒原半兽人,只是粗糙的象征主义加上无意识的意识流拼凑,类似于采样拼贴,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忽然平地一声惊雷,闻得周杰伦的一首《蜗牛》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之列,同时被收入的还有《真心英雄》、《中国人》等多首流行歌曲,不仅鼓掌叫好,也不得不哑然失笑。
听着一个在各种场合吝啬笑容、衣着破烂得考究、眼神迷离得高科技的歌坛小天王,和着动听的旋律清唱“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就算没有人推荐,也根本不会妨碍孩子们随之神魂颠倒,想象自己与偶像一起在精美MTV中化身超级蜗牛,肩负各种版本的美梦,与各种现实的boss争斗,而且正义与胜利当然属于坚持不懈的我方。这一切看上去再正常不过。
有趣之处在于,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这还是第一次,上海市科教党委有关负责人称,民族精神教育决不是说教,要适应儿童少年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而且这次向中学生推荐的100首歌曲主要还是学生喜欢唱的,至于周杰伦的《蜗牛》,入选原因主要是“思想内容十分上进,唱起来琅琅上口”。这不能不让人鼓掌叫好,因为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泛滥的各种流行文化向来是学校严防死守的洪水猛兽,此次既然可以选取一些真正处于流行音乐漩涡中心地带、拥有既成事实霸主地位的歌曲,正大光明地鼓励学生们传唱,了解比不了解强,疏导比围追堵截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鼓励可以成为拥有家长话语权的一方正视青年流行文化存在的一次契机,为更广泛地理解、尊重、鼓励多元化的青年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另一方面,令人哑然失笑的原因则在于,且不说“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的提法是否不大合适的问题,单说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本身,是否又意味着一种不符合青年文化规律的选择呢?好比市面上王二麻子家的糖炒栗子好吃,或者不好吃但吃糖炒栗子正时髦,男女老少早就用嘴和钱包投了票,如果贴出一告示,曰王二麻子家的糖炒栗子味道不错向18岁以下馋嘴孩童严重推荐云云,颇有多此一举之嫌,这还不算张三家孩子与李四家孩子虽然都馋嘴,但可能张三家孩子好甜中带咸,李四家孩子好咸中带甜这种复杂情况。
还有,新问题也冒出来啦。周杰伦不过是一首《蜗牛》入选,按照逻辑这首《蜗牛》必然生存于一堆其他歌曲的CD之中,倘若其他歌曲歌颂情情爱爱的不符合推荐要求,难道要《蜗牛》单独发行一个“爱国主义歌曲推荐”单曲珍藏版?
本报文娱评论员 江海蓝
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这样谈下来结论当然是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圣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圣人又说了:“人人可以象我一样,当圣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过是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都攒下来,用来养浩然正气,结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给皇上进谏有精神了。浩然正气,养着方便又实惠。”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不信人性善简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张海迪。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那么,清朝没有律师却有夹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领导对老百姓的智商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道德水准估计过低呢?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堤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那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碰上了端坐在夹棍从中的知县老爷,众刁民全然没有脾气,只能任打任夹。说让你纳粮你就纳粮,说让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说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你交粮人家还不收,说下班了,还把你着急够呛,大家急不是怕缴不上粮,国库受损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这小子逾期没缴,先别缴了,说你呢说你呢,先别忙着缴了,上来夹一棍子 再缴。你去告人家欺负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伙的:好,发回重审,看老爷不夹死你个龟孙!
这个时候,其实这窝官和一个成功的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这窝官的算计和黑社会的算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两样,都是怎么从这帮子刁民身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对黑社会与官的界定有时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东西能夹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的搜括效率还远在盗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骂倒这些贪官。把大家剃了个秃瓢的官有的时候还是宝贝,百姓一时还舍不得放他走。有个记载说:一个贪官离任,可愁坏了一众百姓,大家都叹气说:好不容易喂肥了一个,现在又要换个空肚鸭来了,可如何了得?
当然,大家最怕的还是流寇。因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样,他们是一锤子买卖,都是宁愿杀羊不愿剪羊毛的主儿。天下大乱的时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祸害,当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这个好光景就是杀羊的变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时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杀人了,改拿棍子夹人,众绵羊一起叹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象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象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上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农业帝国最害怕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偏又最喜欢入侵它,都想来分点土豆吃吃。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或者说土豆力),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把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这些布裁剪成范思哲西服,结果也未必会有两样。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8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当继续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羔羊一个土豆。
《蜗牛》:跑调的德育教材 网友:耿原谅
让周杰伦的歌曲进入教材,笔者觉得有跑调的嫌疑。第一,周杰伦社会公益形象不甚光彩。既然是德育教材,就应该非常注重被选入人物的道德形象、社会公益形象等,周杰伦与很多公益性明星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在一次歌迷见面会上,周杰伦当场在画上签下大大的脏字,“这是现在年轻人的用语。现在年轻人都很开放,而我用这个字表达比好还要好的意思”,不把脏话当脏话,反而解释成优秀之意,再加上周杰伦与蔡依林、侯佩岑绯闻不断等,将他选入德育教材,就等于认可了他不够优秀、不够坦荡的不负责的恶俗行为,这会鼓励孩子模仿,形成负面引导,如果学生都学着用脏话赞美人,绯闻不断,校园德育方向会引向何方?
第二,歌词主题与爱国主题不甚合拍。既然是爱国主义教材,就更应注重教材的严肃性和民族性,多选用慷慨悲壮、震撼人心的人和事,可看看《蜗牛》,与其说是爱国歌曲,不如说是励志歌曲:“该不该搁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在最高点撑着夜往前飞。”词写得很好,但与爱国主题似乎有点远了。
第三,审美观念的误导。德育教材不仅包含德育内涵,还包括美育内涵,将《蜗牛》选入教材,无疑是在想学生说,这是优秀艺术,可是目前,人们对周杰伦的艺术成就还存在着很大争议,笔者仔细玩味周的音乐,我只听到了激越节奏和“周氏特色”的咬字不清,声乐审美的起码标准咬字清晰、字正腔圆都做不到。
以“爱国”的名义将爱国主义贬值 网友:直言了
咱要问:若“琅琅上口”上口就是爱国主义歌曲,那“何日君再来”更上口,早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了,为啥不编入?再说,“何日君再来”的中国诗歌味道十足,是纯粹的中国语言文字写成的,曲调也是典型的中国乐曲。而《蜗牛》呢,歌词夹杂了英文、语言文字不伦不类;曲调处理受日本酒吧歌曲的影响很明显,这叫啥“爱国主义歌曲”?比较起来,“何日君再来”是比《蜗牛》更合格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更还有,如果“琅琅上口”就是“爱国”的话,那么,“台独”们编造的顺口溜东西也是“琅琅上口”,那是不是也可以编入“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了?
爱国主义教育是本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精神的政治教育,当然就要用本国的政治情感、本国的文化语言和本国的情调作为选择歌曲的标准内容,而不是看某某歌曲是否“琅琅上口”。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在国家蒙受危难和战争的时候的保卫国家的情操,是在国家获得或需要国际社会承认和尊敬的时候的为国家感到自豪和为国家祝福的情操。这样的情操并非是在任何时候和用任何方式都可以使用的。
这些年来呢,不少机构、公司、团体和个人,明明是为自己的商业利益而搞推销,却要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一些“海归”明明是为了个人生活原因而选择回国,却也带个“爱国主义”的帽子。这不,为了推销港台明星,又打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号把不伦不类的流行歌曲列入“爱国主义教育”了。在“爱国”的名义下,爱国主义已经被贬值成了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奴仆,还要贬到啥地步才算罢休啊?
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这样谈下来结论当然是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圣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圣人又说了:“人人可以象我一样,当圣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过是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都攒下来,用来养浩然正气,结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给皇上进谏有精神了。浩然正气,养着方便又实惠。”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不信人性善简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张海迪。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那么,清朝没有律师却有夹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领导对老百姓的智商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道德水准估计过低呢?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堤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那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碰上了端坐在夹棍从中的知县老爷,众刁民全然没有脾气,只能任打任夹。说让你纳粮你就纳粮,说让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说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你交粮人家还不收,说下班了,还把你着急够呛,大家急不是怕缴不上粮,国库受损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这小子逾期没缴,先别缴了,说你呢说你呢,先别忙着缴了,上来夹一棍子 再缴。你去告人家欺负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伙的:好,发回重审,看老爷不夹死你个龟孙!
这个时候,其实这窝官和一个成功的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这窝官的算计和黑社会的算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两样,都是怎么从这帮子刁民身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对黑社会与官的界定有时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东西能夹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的搜括效率还远在盗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骂倒这些贪官。把大家剃了个秃瓢的官有的时候还是宝贝,百姓一时还舍不得放他走。有个记载说:一个贪官离任,可愁坏了一众百姓,大家都叹气说:好不容易喂肥了一个,现在又要换个空肚鸭来了,可如何了得?
当然,大家最怕的还是流寇。因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样,他们是一锤子买卖,都是宁愿杀羊不愿剪羊毛的主儿。天下大乱的时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祸害,当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这个好光景就是杀羊的变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时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杀人了,改拿棍子夹人,众绵羊一起叹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象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象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上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农业帝国最害怕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偏又最喜欢入侵它,都想来分点土豆吃吃。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或者说土豆力),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把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这些布裁剪成范思哲西服,结果也未必会有两样。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8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当继续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羔羊一个土豆。
《蜗牛》:跑调的德育教材 网友:耿原谅
让周杰伦的歌曲进入教材,笔者觉得有跑调的嫌疑。第一,周杰伦社会公益形象不甚光彩。既然是德育教材,就应该非常注重被选入人物的道德形象、社会公益形象等,周杰伦与很多公益性明星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在一次歌迷见面会上,周杰伦当场在画上签下大大的脏字,“这是现在年轻人的用语。现在年轻人都很开放,而我用这个字表达比好还要好的意思”,不把脏话当脏话,反而解释成优秀之意,再加上周杰伦与蔡依林、侯佩岑绯闻不断等,将他选入德育教材,就等于认可了他不够优秀、不够坦荡的不负责的恶俗行为,这会鼓励孩子模仿,形成负面引导,如果学生都学着用脏话赞美人,绯闻不断,校园德育方向会引向何方?
第二,歌词主题与爱国主题不甚合拍。既然是爱国主义教材,就更应注重教材的严肃性和民族性,多选用慷慨悲壮、震撼人心的人和事,可看看《蜗牛》,与其说是爱国歌曲,不如说是励志歌曲:“该不该搁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在最高点撑着夜往前飞。”词写得很好,但与爱国主题似乎有点远了。
第三,审美观念的误导。德育教材不仅包含德育内涵,还包括美育内涵,将《蜗牛》选入教材,无疑是在想学生说,这是优秀艺术,可是目前,人们对周杰伦的艺术成就还存在着很大争议,笔者仔细玩味周的音乐,我只听到了激越节奏和“周氏特色”的咬字不清,声乐审美的起码标准咬字清晰、字正腔圆都做不到。
以“爱国”的名义将爱国主义贬值 网友:直言了
咱要问:若“琅琅上口”上口就是爱国主义歌曲,那“何日君再来”更上口,早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了,为啥不编入?再说,“何日君再来”的中国诗歌味道十足,是纯粹的中国语言文字写成的,曲调也是典型的中国乐曲。而《蜗牛》呢,歌词夹杂了英文、语言文字不伦不类;曲调处理受日本酒吧歌曲的影响很明显,这叫啥“爱国主义歌曲”?比较起来,“何日君再来”是比《蜗牛》更合格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更还有,如果“琅琅上口”就是“爱国”的话,那么,“台独”们编造的顺口溜东西也是“琅琅上口”,那是不是也可以编入“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了?
爱国主义教育是本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精神的政治教育,当然就要用本国的政治情感、本国的文化语言和本国的情调作为选择歌曲的标准内容,而不是看某某歌曲是否“琅琅上口”。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在国家蒙受危难和战争的时候的保卫国家的情操,是在国家获得或需要国际社会承认和尊敬的时候的为国家感到自豪和为国家祝福的情操。这样的情操并非是在任何时候和用任何方式都可以使用的。
这些年来呢,不少机构、公司、团体和个人,明明是为自己的商业利益而搞推销,却要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一些“海归”明明是为了个人生活原因而选择回国,却也带个“爱国主义”的帽子。这不,为了推销港台明星,又打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号把不伦不类的流行歌曲列入“爱国主义教育”了。在“爱国”的名义下,爱国主义已经被贬值成了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奴仆,还要贬到啥地步才算罢休啊?
周杰伦爬向“先进文化” 与妞妞电影及“政府”的背后
云淡水暖
报载“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上传出这样的消息,台湾地区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刚刚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这还是第一次,重要的是,还有像《蜗牛》这样被学生广泛传唱的,这也是破天荒的。”,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上海的世界愈发让人“耳目一新”了,草民不知道“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由谁主办,但肯定跑不了教育、宣传这样的政府、官方机构。
说实话,周杰伦也好、其他的什么“腕”、“星”也罢,如果要开“个唱”,有FANS觅死觅活,尖叫疯癫,乃至于“冲破护卫”,袭脸、袭胸,都算不得什么新闻,或者周杰伦被狗仔队偷拍到又与某闺秀、某碧玉偷欢亲热了,也算不得什么新鲜,因为在当今的媒体语境中,这些东西已经几近垃圾,台湾人讲就是“勒佘”,形象的说,就是“狗咬人”,毫无轰动效应了。而偏偏由“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把周的《蜗牛》选为“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这个“幽默”就“黑”的太深了,形象的说,就是“人咬狗”,难怪人民网的首页出了专题“政府推荐周杰伦《蜗牛》成爱国歌曲”,更难怪网上、媒体热议不断。
如果说,因为“被学生广泛传唱”而要迎合青少年的业余喜好,不妨推荐为“青少年喜爱的流行歌曲”云云,这没有什么异议,也算不得“人咬狗”,但冠以“爱国主义歌曲”的名头往外拿,就显得对“爱国主义”的轻薄甚至是亵渎,浅了说,玩笑开大了,深了说,别有用心,这样的“爱国主义”,无根无源。举个例子,当年,日寇大兵压境,同胞生灵涂炭,也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有人唱“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祖国的栋梁”,也有人唱“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从流行的程度看,《桃花江》不比《毕业歌》小,甚至迅速传唱到全国,演唱的“歌舞团”所到之处,应者如云,不亚于今天“蜗牛”们的“个唱”,谁算“爱国歌曲”?
消息说“记者采访了周杰伦公司以及相关人士,整体上来说,业内人士都很赞同,而网民和不少普通读者听众则持很大的反对意见。”,草民猜想,所谓“业内人士”,一种是男一头长发而女差不多秃瓢,穿着怪异,不分雌雄耳朵上均吊着耳环的“另类”们,臭味相投;另外一种是唯恐天下无“人咬狗”,自我张扬到极致,视人间只有其最“理性”的老资、小资、“娱记”帮闲们。“网民和不少普通读者听众”的声音,则是上不了主流平台的。
草民不知道周杰伦“爱”的是哪一“国”,一般说来,既然是“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所“隆重推出”,这个“国”应该是中国,对大陆艺人来说,首先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虑到周的身份,起码应该是“一个中国”的“国”,在今天的台湾语境下面,“绿”也好,“蓝”也罢,要么对“一个中国”视如洪水猛兽,要么就讳莫如深,艺人们到大陆来,是来赚钱的,对于“爱国”这样的内涵,基本是回避,打哈哈,最多说是“中性”而已,其处境我们理解,在商言商,在艺言艺,但干嘛要上赶着奉以一顶“爱国”的含有太多的感情寄托的桂冠?港台演员演唱的歌曲,谈得上“爱国”的,草民倒是依稀记得几句,比如“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我们从周杰伦的哪一首歌中体味到了“一个中国”,《蜗牛》又爬出来什么“爱国”?草民找来《蜗牛》的录音听过,还是惯常的颓唐的哼唧,玩世不恭,含糊的咬字,唯一可以清晰地解构出来的句子,就是“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爬”什么,爬自己头上有“一片小小的蓝天”,充其量是自我中心意识指引下的自我奋斗中的呻吟,而“此次选取曲目的负责人王月萍”们居然可以听出”有利于爱国主义的传承”的博大,与“这个选择和创意非常好,不仅思想内容好,而且非常上口。”的高度赞许,简直是匪夷所思,可能有人说,不就是一首唱了几天过后就不记得的“流行歌”么,何必“上纲上线”,问题在于,提出“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这样的举动,本身就是上了“纲”,在了“线”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从“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这还是第一次,”中,草民仿佛又看到了另外一桩以政府官方之名向学生进行的“推荐”,那次,某市市委宣传部、教育局、市文化局、共青团市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发通知,向各中学“推荐”,各学校让初一、初二、初三的学生们“自愿掏钱”“踊跃观看”“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生动可爱的精神、气质和风貌,是一部反映现代青少年成长的好片。”的“最昂贵的青春偶像剧”,也是热议不断,其中的关键是集投资者、编剧、主演于一身的妞妞的令人乍舌的富有和背景。在进一步引伸出事件背后的商业追求。
周杰伦的《蜗牛》在爬和妞妞耗资巨大的留学飞行于英伦,表面上事件的性质各异,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个人的“成功”,而这“成功”的显著标志,就是金钱所表达的价值。抛开妞妞“成功”背后所必定拥有的财富底蕴,只看改革开放以来风靡于世、特别是风靡于青少年当中的港台、日韩歌星、舞星、影星们的“成功”与否,衡量的标志也无非是钱。在这个语境中被包围、被诱导、被陶醉、被疯狂的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们,知道了钱的“至高无上”与“无所不能”,围绕着钱,“星”们可以为所欲为,天马行空,潜移默化之下,那些低俗、浅薄、只要有钱“包装”就可以“爬”出自己的“一片蓝天”的梦幻,造就了畸形的心态。如果周杰伦“爬”了半天,还是一个“赤足走在田埂上”的劳作农人,如果F4“爬”了半天还是贩夫走卒,还有那么些逐臭如蝇的娱记及其煽动下的FANS们么,现代流行娱乐,不过是金钱驱使下的,靠拨动青少年追名逐利欲望和发泄的游戏而已。
问题在于“政府”的不甘寂寞的错位,妞妞电影事件中有权势与金钱交错下的错位,周杰伦“爱国”中的就可能是选题者们认知的错位。相比之下,可能美国人就比我们的某些人分的清“爱国”与“娱乐”的界限,在美国人的影视剧中,“爱国”的主题,总是以“正剧”的形式出现。
像“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这样的场合,像某市市委宣传部、教育局、市文化局、共青团市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委,绝对应该大讲“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文化的代表”的原则的。可是,他们交出的却是《蜗牛》的“爬”与飞翔在英伦的“绵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周杰伦爬向“先进文化” 与妞妞电影及“政府”的背后
云淡水暖
报载“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上传出这样的消息,台湾地区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刚刚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这还是第一次,重要的是,还有像《蜗牛》这样被学生广泛传唱的,这也是破天荒的。”,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上海的世界愈发让人“耳目一新”了,草民不知道“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由谁主办,但肯定跑不了教育、宣传这样的政府、官方机构。
说实话,周杰伦也好、其他的什么“腕”、“星”也罢,如果要开“个唱”,有FANS觅死觅活,尖叫疯癫,乃至于“冲破护卫”,袭脸、袭胸,都算不得什么新闻,或者周杰伦被狗仔队偷拍到又与某闺秀、某碧玉偷欢亲热了,也算不得什么新鲜,因为在当今的媒体语境中,这些东西已经几近垃圾,台湾人讲就是“勒佘”,形象的说,就是“狗咬人”,毫无轰动效应了。而偏偏由“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把周的《蜗牛》选为“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这个“幽默”就“黑”的太深了,形象的说,就是“人咬狗”,难怪人民网的首页出了专题“政府推荐周杰伦《蜗牛》成爱国歌曲”,更难怪网上、媒体热议不断。
如果说,因为“被学生广泛传唱”而要迎合青少年的业余喜好,不妨推荐为“青少年喜爱的流行歌曲”云云,这没有什么异议,也算不得“人咬狗”,但冠以“爱国主义歌曲”的名头往外拿,就显得对“爱国主义”的轻薄甚至是亵渎,浅了说,玩笑开大了,深了说,别有用心,这样的“爱国主义”,无根无源。举个例子,当年,日寇大兵压境,同胞生灵涂炭,也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有人唱“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祖国的栋梁”,也有人唱“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从流行的程度看,《桃花江》不比《毕业歌》小,甚至迅速传唱到全国,演唱的“歌舞团”所到之处,应者如云,不亚于今天“蜗牛”们的“个唱”,谁算“爱国歌曲”?
消息说“记者采访了周杰伦公司以及相关人士,整体上来说,业内人士都很赞同,而网民和不少普通读者听众则持很大的反对意见。”,草民猜想,所谓“业内人士”,一种是男一头长发而女差不多秃瓢,穿着怪异,不分雌雄耳朵上均吊着耳环的“另类”们,臭味相投;另外一种是唯恐天下无“人咬狗”,自我张扬到极致,视人间只有其最“理性”的老资、小资、“娱记”帮闲们。“网民和不少普通读者听众”的声音,则是上不了主流平台的。
草民不知道周杰伦“爱”的是哪一“国”,一般说来,既然是“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所“隆重推出”,这个“国”应该是中国,对大陆艺人来说,首先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虑到周的身份,起码应该是“一个中国”的“国”,在今天的台湾语境下面,“绿”也好,“蓝”也罢,要么对“一个中国”视如洪水猛兽,要么就讳莫如深,艺人们到大陆来,是来赚钱的,对于“爱国”这样的内涵,基本是回避,打哈哈,最多说是“中性”而已,其处境我们理解,在商言商,在艺言艺,但干嘛要上赶着奉以一顶“爱国”的含有太多的感情寄托的桂冠?港台演员演唱的歌曲,谈得上“爱国”的,草民倒是依稀记得几句,比如“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我们从周杰伦的哪一首歌中体味到了“一个中国”,《蜗牛》又爬出来什么“爱国”?草民找来《蜗牛》的录音听过,还是惯常的颓唐的哼唧,玩世不恭,含糊的咬字,唯一可以清晰地解构出来的句子,就是“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爬”什么,爬自己头上有“一片小小的蓝天”,充其量是自我中心意识指引下的自我奋斗中的呻吟,而“此次选取曲目的负责人王月萍”们居然可以听出”有利于爱国主义的传承”的博大,与“这个选择和创意非常好,不仅思想内容好,而且非常上口。”的高度赞许,简直是匪夷所思,可能有人说,不就是一首唱了几天过后就不记得的“流行歌”么,何必“上纲上线”,问题在于,提出“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这样的举动,本身就是上了“纲”,在了“线”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从“由政府部门出面向学生推荐歌曲这还是第一次,”中,草民仿佛又看到了另外一桩以政府官方之名向学生进行的“推荐”,那次,某市市委宣传部、教育局、市文化局、共青团市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委联合颁发通知,向各中学“推荐”,各学校让初一、初二、初三的学生们“自愿掏钱”“踊跃观看”“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生动可爱的精神、气质和风貌,是一部反映现代青少年成长的好片。”的“最昂贵的青春偶像剧”,也是热议不断,其中的关键是集投资者、编剧、主演于一身的妞妞的令人乍舌的富有和背景。在进一步引伸出事件背后的商业追求。
周杰伦的《蜗牛》在爬和妞妞耗资巨大的留学飞行于英伦,表面上事件的性质各异,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个人的“成功”,而这“成功”的显著标志,就是金钱所表达的价值。抛开妞妞“成功”背后所必定拥有的财富底蕴,只看改革开放以来风靡于世、特别是风靡于青少年当中的港台、日韩歌星、舞星、影星们的“成功”与否,衡量的标志也无非是钱。在这个语境中被包围、被诱导、被陶醉、被疯狂的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们,知道了钱的“至高无上”与“无所不能”,围绕着钱,“星”们可以为所欲为,天马行空,潜移默化之下,那些低俗、浅薄、只要有钱“包装”就可以“爬”出自己的“一片蓝天”的梦幻,造就了畸形的心态。如果周杰伦“爬”了半天,还是一个“赤足走在田埂上”的劳作农人,如果F4“爬”了半天还是贩夫走卒,还有那么些逐臭如蝇的娱记及其煽动下的FANS们么,现代流行娱乐,不过是金钱驱使下的,靠拨动青少年追名逐利欲望和发泄的游戏而已。
问题在于“政府”的不甘寂寞的错位,妞妞电影事件中有权势与金钱交错下的错位,周杰伦“爱国”中的就可能是选题者们认知的错位。相比之下,可能美国人就比我们的某些人分的清“爱国”与“娱乐”的界限,在美国人的影视剧中,“爱国”的主题,总是以“正剧”的形式出现。
像“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这样的场合,像某市市委宣传部、教育局、市文化局、共青团市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委,绝对应该大讲“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文化的代表”的原则的。可是,他们交出的却是《蜗牛》的“爬”与飞翔在英伦的“绵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数年前我曾对所了解的官场某部份下了一个评语:不学无术加胆大包天。现在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一切东西的改变,首先是让人取得一个参照物作为观察点,当所有的东西都同步运动时,应该没有改变的感觉的。可这世界确实在变,而且是各行各业各方各面与时俱进的改变。因而当自己对它感觉惊诧时,只能说明自己作为参照物的这颗心没能与时俱进。世界真的越来越陌生了,爱国主义的定义不知也进化到什么样的程度?至少上海当局的这一举措,是把蜗牛精神纳进去了。“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这怎么听怎么看都象黄梁梦中的理想?
释迦牟尼说:末法之世,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原来佛所谓的邪师,不一定非得披了袈裟的才算。
[em06][em06][em06]
数年前我曾对所了解的官场某部份下了一个评语:不学无术加胆大包天。现在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一切东西的改变,首先是让人取得一个参照物作为观察点,当所有的东西都同步运动时,应该没有改变的感觉的。可这世界确实在变,而且是各行各业各方各面与时俱进的改变。因而当自己对它感觉惊诧时,只能说明自己作为参照物的这颗心没能与时俱进。世界真的越来越陌生了,爱国主义的定义不知也进化到什么样的程度?至少上海当局的这一举措,是把蜗牛精神纳进去了。“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这怎么听怎么看都象黄梁梦中的理想?
释迦牟尼说:末法之世,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原来佛所谓的邪师,不一定非得披了袈裟的才算。
[em06][em06][em06]
个人观点,周的歌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如:东风破.晴天这两首)
在当今的流行乐坛,这样的歌,能得到我的接受和欣赏.
包括旋律和词.我都属于欣赏一类.
我没关注国内媒体是具体怎样评价关于收编这个事件的(但据说好象是网上骂声连连)
发表个个人观点.找周的歌收编,总比找谢听风的要好NNNNN多倍.
周同志多首歌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描写,很不错.
总比,一天到晚爱个不停的谢听风要好很多很多.
收编了周的歌,大家也不用多讨论什么,有突破有进步,对于中国的教育业来说,何尝不是好事一件.
纯属个人观点.
个人观点,周的歌我还是比较欣赏的(如:东风破.晴天这两首)
在当今的流行乐坛,这样的歌,能得到我的接受和欣赏.
包括旋律和词.我都属于欣赏一类.
我没关注国内媒体是具体怎样评价关于收编这个事件的(但据说好象是网上骂声连连)
发表个个人观点.找周的歌收编,总比找谢听风的要好NNNNN多倍.
周同志多首歌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描写,很不错.
总比,一天到晚爱个不停的谢听风要好很多很多.
收编了周的歌,大家也不用多讨论什么,有突破有进步,对于中国的教育业来说,何尝不是好事一件.
纯属个人观点.
与阿穆同感,喜欢《东风破》的调调,虽然听不太清楚歌词,但很中国。
还有早先的一首《龙卷风》。[em05]
与阿穆同感,喜欢《东风破》的调调,虽然听不太清楚歌词,但很中国。
还有早先的一首《龙卷风》。[em05]
好的东西自然能流传,破烂玩意儿不会长久,没必要煞有介事地鼓掌或谩骂.本来就没必要搞什么"推荐",音乐不是靠"推荐"来让人接受的,其他许多东西也如此,比如爱国情怀.
好的东西自然能流传,破烂玩意儿不会长久,没必要煞有介事地鼓掌或谩骂.本来就没必要搞什么"推荐",音乐不是靠"推荐"来让人接受的,其他许多东西也如此,比如爱国情怀.
现在爱不爱国是他们说的,但算不算是历史说的!顺便转一说《东方之珠》不爱国的:
光明网 - 光明观察 - 网络评论
警惕流行歌曲中的种族主义——从《蜗牛》等歌曲入选爱国主义歌曲说起
陶东风
近日由于周杰伦的《蜗牛》、刘德华的《中国人》和组群的《真心英雄》入选上海市教育机构推荐的“中学生爱国主义推荐歌曲”,引起了各界的纷纷议论。对这三首妇孺皆知的流行歌曲,我虽早有耳闻,却不记得歌词的全部,于是把三首歌的歌词找来认真看/听了一遍,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所有关于这次事件的评论中,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家都围绕周杰伦的《蜗牛》在说事:批评者把矛盾对准它说它无何与爱国无关,赞成者也在一个劲论证它为什么可以入选。大家一致“冷落”的是《中国人》和《真心英雄》。似乎它们的入选是无可非议的,根本用不着讨论。
仔细阅读了这三首歌的歌词以后,我觉得《蜗牛》与《真心英雄》的入选虽然有些勉强却无大碍,最不该入选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蜗牛》与《真心英雄》的主题是颂扬一种比较健康的人生观。《蜗牛》突出小人物的理想情怀和上进精神(“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真心英雄》表现平凡人的友谊与博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以及乐观面对困难、努力向上的精神(“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底流动”),虽然与以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确没有太大关联,但是它表现的毕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人生观,把它纳入爱国主义这个筐中,虽嫌勉强却也不至于误导国人对于爱国主义的理解。但《中国人》就不同了。这首歌似乎是与爱国主题关系最紧密(一看题目就知道),但却明显存在种族主义倾向。歌词中直接与所谓“中国人”身份相关的是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这句(“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这里所突出的是以“中国人”的生理学特征为标志的种族身份,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更不是中国人的公民身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种族共同体,绝大多数的现代民族-国家都是按照现代政治原则组织起来的多种族政治共同体。这个现代政治原则就是:各不同的民族/种族应该在普遍(无论什么种族)公民权利基础上形成对于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这种认同之所以是现代的,是因为它不同于建立在皮肤、头发、眼睛等人种特征以及特定的山脉、河流名称(如“长江”“黄河”)之上的前现代认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我们把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同建立在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等人种特征之上,那么,我们要问:加入了中国籍的西方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是否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认同以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为认同符号的“爱国主义”呢?还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东北的俄国人也不乏褐眼睛、蓝眼睛、黄头发者,他们是否是中国人?说得严重一点,这样的“爱国主义”无异于是在不自觉地鼓吹民族分离,承认那些皮肤不黄、眼睛不黑的中国公民不是中国人!
其实这种以“爱国主义”名义表现种族主义实质的流行歌曲还不少,而且大多被当成表现“爱国主义”的好歌广为传唱。比如《东方之珠》(演唱:陈淑桦,词 曲:罗大佑)就是。这首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同样也在宣扬狭隘的种族主义,因为“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表明这个“中国人”是通过生理特征界定的。还有那首唱遍全国的《龙的传人》(张明敏等)也是。这首歌里的“龙的传人”最多只能说是汉人,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汉人”当然不是“中国人”的同义词),因为他的特点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如果我们把歌词中的“中国人”理解为现代中国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么,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有些中国人不仅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而且根本不是“龙的传人”:他们的图腾不是龙,也不是长江或黄河的子孙。他们有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民族传说与图腾,有自己的母亲河和神灵山,但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这样的标准,不仅仅流行歌词,其他各种报刊文章甚至官方社论中恐怕都存在把具有特定生理、地理 、文化内涵的种族认同符号不恰当地当作民族国家认同符号的政治性错误。
更有甚者,《亲爱的中国我爱你》(叶凡)赤裸裸地说什么“黄皮肤的脸是面中国旗”(整个歌词是:“我来到世上就选择了你/和我一样的人有几十亿/无论是领袖还是人民/都是你爱着的孩子/我走到那里都充满勇气/黄皮肤的脸是面中国旗/不管有痛苦还是欢乐/我都想告诉你/你不说一句话/却不时不把我激励/就因为你在我心里/我的眼中从来没有悲哀的泪滴/亲爱的亲爱的中国我爱你/我越是爱你越就懂得五千年的风和雨/我越是爱你越就知道谁也没有你美丽”)。把国旗等于“黄皮肤的脸”实在是令人吃惊的无知!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国旗怎么能够凝聚起中华人民国土地上的白皮肤红皮肤乃至黑皮肤的中国公民?难道你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还是鼓励他们去搞分裂闹独立?
现在爱不爱国是他们说的,但算不算是历史说的!顺便转一说《东方之珠》不爱国的:
光明网 - 光明观察 - 网络评论
警惕流行歌曲中的种族主义——从《蜗牛》等歌曲入选爱国主义歌曲说起
陶东风
近日由于周杰伦的《蜗牛》、刘德华的《中国人》和组群的《真心英雄》入选上海市教育机构推荐的“中学生爱国主义推荐歌曲”,引起了各界的纷纷议论。对这三首妇孺皆知的流行歌曲,我虽早有耳闻,却不记得歌词的全部,于是把三首歌的歌词找来认真看/听了一遍,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所有关于这次事件的评论中,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家都围绕周杰伦的《蜗牛》在说事:批评者把矛盾对准它说它无何与爱国无关,赞成者也在一个劲论证它为什么可以入选。大家一致“冷落”的是《中国人》和《真心英雄》。似乎它们的入选是无可非议的,根本用不着讨论。
仔细阅读了这三首歌的歌词以后,我觉得《蜗牛》与《真心英雄》的入选虽然有些勉强却无大碍,最不该入选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蜗牛》与《真心英雄》的主题是颂扬一种比较健康的人生观。《蜗牛》突出小人物的理想情怀和上进精神(“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真心英雄》表现平凡人的友谊与博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以及乐观面对困难、努力向上的精神(“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底流动”),虽然与以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确没有太大关联,但是它表现的毕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人生观,把它纳入爱国主义这个筐中,虽嫌勉强却也不至于误导国人对于爱国主义的理解。但《中国人》就不同了。这首歌似乎是与爱国主题关系最紧密(一看题目就知道),但却明显存在种族主义倾向。歌词中直接与所谓“中国人”身份相关的是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这句(“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这里所突出的是以“中国人”的生理学特征为标志的种族身份,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更不是中国人的公民身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种族共同体,绝大多数的现代民族-国家都是按照现代政治原则组织起来的多种族政治共同体。这个现代政治原则就是:各不同的民族/种族应该在普遍(无论什么种族)公民权利基础上形成对于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这种认同之所以是现代的,是因为它不同于建立在皮肤、头发、眼睛等人种特征以及特定的山脉、河流名称(如“长江”“黄河”)之上的前现代认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我们把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同建立在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等人种特征之上,那么,我们要问:加入了中国籍的西方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是否中国人?他们怎么能够认同以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为认同符号的“爱国主义”呢?还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东北的俄国人也不乏褐眼睛、蓝眼睛、黄头发者,他们是否是中国人?说得严重一点,这样的“爱国主义”无异于是在不自觉地鼓吹民族分离,承认那些皮肤不黄、眼睛不黑的中国公民不是中国人!
其实这种以“爱国主义”名义表现种族主义实质的流行歌曲还不少,而且大多被当成表现“爱国主义”的好歌广为传唱。比如《东方之珠》(演唱:陈淑桦,词 曲:罗大佑)就是。这首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同样也在宣扬狭隘的种族主义,因为“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表明这个“中国人”是通过生理特征界定的。还有那首唱遍全国的《龙的传人》(张明敏等)也是。这首歌里的“龙的传人”最多只能说是汉人,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汉人”当然不是“中国人”的同义词),因为他的特点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如果我们把歌词中的“中国人”理解为现代中国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么,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有些中国人不仅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而且根本不是“龙的传人”:他们的图腾不是龙,也不是长江或黄河的子孙。他们有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民族传说与图腾,有自己的母亲河和神灵山,但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这样的标准,不仅仅流行歌词,其他各种报刊文章甚至官方社论中恐怕都存在把具有特定生理、地理 、文化内涵的种族认同符号不恰当地当作民族国家认同符号的政治性错误。
更有甚者,《亲爱的中国我爱你》(叶凡)赤裸裸地说什么“黄皮肤的脸是面中国旗”(整个歌词是:“我来到世上就选择了你/和我一样的人有几十亿/无论是领袖还是人民/都是你爱着的孩子/我走到那里都充满勇气/黄皮肤的脸是面中国旗/不管有痛苦还是欢乐/我都想告诉你/你不说一句话/却不时不把我激励/就因为你在我心里/我的眼中从来没有悲哀的泪滴/亲爱的亲爱的中国我爱你/我越是爱你越就懂得五千年的风和雨/我越是爱你越就知道谁也没有你美丽”)。把国旗等于“黄皮肤的脸”实在是令人吃惊的无知!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国旗怎么能够凝聚起中华人民国土地上的白皮肤红皮肤乃至黑皮肤的中国公民?难道你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还是鼓励他们去搞分裂闹独立?
等周杰伦“退流行”后再说…… -------------------------------------------------------------------------------- 文 高芾 东方早报 2005-3-29
本来,我已经发誓不谈周杰伦和他的爱国主义歌曲。一位先生在报上评论说,周杰伦口齿不清,教他的歌,会出现一大帮口齿不清支支吾吾的小孩,这些口齿不清支支吾吾的小孩怎么爱国家爱民族?他不敢想象。我不敢谈这事,就是怕人家以为我和这种人是一拨儿的。 还有一位先生在网上评论说:“就好像那些董小宛、柳如是们,虽然也是风流人物,不乏文人骚客称扬,体现我们的自由多元,但是要把他们列入清史、明史类的人物传,总不免有点那个。”有点那个?哪个啊?不能再往下扯,再扯就更乱了。 我有时会想:周杰伦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到底哪方面触犯了反对者脆弱的神经?是大众性吗?反对金庸进教科书,却没有人谈论同时进入的王度庐,同样,好像也没人反对《真心英雄》成为爱国主义歌曲……还是周杰伦、金庸像刘翔一样,成名时间太短,缺乏足够的时间检验他们是否堪称模范和榜样? 我相信,如果没有“爱国主义”这个冠名,只是“推荐曲目”,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不爽。可是,周杰伦的歌还需要推荐吗?那么多签唱会代言会歌迷见面会,又不是白搞的。教育部门不是电台DJ,似乎没有必要把本来就流行的东西,再向流行文化消费主要人群推荐一次。 当然,我理解教育部门的苦心:喜闻乐见嘛,与时俱进嘛,贴近生活嘛。还有一条,不知道始作俑者有没有想到:选周杰伦的歌一定会引起媒体关注,进而公众争论,进而提高本次德育活动知名度,进而……我大概是被商业社会把心眼带坏了,看什么都像是策划。 其实我真的希望教育部门能向中学生们推荐一些经典的“学堂乐歌”。自从上世纪初中小学堂在全国各地普及,学堂乐歌就开始了它的传统。第一首据说是《男儿第一志气高》,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李叔同填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有人会说,那些歌都老掉牙了,小朋友们准不喜欢。喜欢不喜欢那是后话,现在的状况是他们根本听不到那些曾经“感动中国”的歌,生活中只有隆重推出唾手可得的消费产品,所以也无从选择。现在提倡素质教育,独立思考,为什么要剥夺小朋友自由选择的权利呢?教育部门既然是公共服务机构,就像公共电视,理应提供一些与流行文化不一样的资源。 我没有看见教育部门的推荐目录全文,说不定这些歌都已经在里面了。如果真是那样,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我觉得教育部门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职能和VJ、DJ们区别一下。流行歌曲入中小学教材,台湾有过这样的例子,但多少会和当下保持一点距离。比如李子恒词曲、刘文正首唱的《秋蝉》:“听我把春水叫寒,听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幽幽……”这样的歌词不怎么上进,也没有教人爱祖国爱人民,但可以让人体会到汉语的美感,我看归入“爱国主义歌曲”也没什么不可以。周杰伦的歌,尤其是方文山的词,也能有这样的效果,不过,我们可不可以等这些歌“退流行”之后,不再是媒体热播热炒的话题之后,再用推荐的方式向他们致敬?
等周杰伦“退流行”后再说…… -------------------------------------------------------------------------------- 文 高芾 东方早报 2005-3-29
本来,我已经发誓不谈周杰伦和他的爱国主义歌曲。一位先生在报上评论说,周杰伦口齿不清,教他的歌,会出现一大帮口齿不清支支吾吾的小孩,这些口齿不清支支吾吾的小孩怎么爱国家爱民族?他不敢想象。我不敢谈这事,就是怕人家以为我和这种人是一拨儿的。 还有一位先生在网上评论说:“就好像那些董小宛、柳如是们,虽然也是风流人物,不乏文人骚客称扬,体现我们的自由多元,但是要把他们列入清史、明史类的人物传,总不免有点那个。”有点那个?哪个啊?不能再往下扯,再扯就更乱了。 我有时会想:周杰伦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到底哪方面触犯了反对者脆弱的神经?是大众性吗?反对金庸进教科书,却没有人谈论同时进入的王度庐,同样,好像也没人反对《真心英雄》成为爱国主义歌曲……还是周杰伦、金庸像刘翔一样,成名时间太短,缺乏足够的时间检验他们是否堪称模范和榜样? 我相信,如果没有“爱国主义”这个冠名,只是“推荐曲目”,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不爽。可是,周杰伦的歌还需要推荐吗?那么多签唱会代言会歌迷见面会,又不是白搞的。教育部门不是电台DJ,似乎没有必要把本来就流行的东西,再向流行文化消费主要人群推荐一次。 当然,我理解教育部门的苦心:喜闻乐见嘛,与时俱进嘛,贴近生活嘛。还有一条,不知道始作俑者有没有想到:选周杰伦的歌一定会引起媒体关注,进而公众争论,进而提高本次德育活动知名度,进而……我大概是被商业社会把心眼带坏了,看什么都像是策划。 其实我真的希望教育部门能向中学生们推荐一些经典的“学堂乐歌”。自从上世纪初中小学堂在全国各地普及,学堂乐歌就开始了它的传统。第一首据说是《男儿第一志气高》,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李叔同填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有人会说,那些歌都老掉牙了,小朋友们准不喜欢。喜欢不喜欢那是后话,现在的状况是他们根本听不到那些曾经“感动中国”的歌,生活中只有隆重推出唾手可得的消费产品,所以也无从选择。现在提倡素质教育,独立思考,为什么要剥夺小朋友自由选择的权利呢?教育部门既然是公共服务机构,就像公共电视,理应提供一些与流行文化不一样的资源。 我没有看见教育部门的推荐目录全文,说不定这些歌都已经在里面了。如果真是那样,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我觉得教育部门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职能和VJ、DJ们区别一下。流行歌曲入中小学教材,台湾有过这样的例子,但多少会和当下保持一点距离。比如李子恒词曲、刘文正首唱的《秋蝉》:“听我把春水叫寒,听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幽幽……”这样的歌词不怎么上进,也没有教人爱祖国爱人民,但可以让人体会到汉语的美感,我看归入“爱国主义歌曲”也没什么不可以。周杰伦的歌,尤其是方文山的词,也能有这样的效果,不过,我们可不可以等这些歌“退流行”之后,不再是媒体热播热炒的话题之后,再用推荐的方式向他们致敬?
世道注定要变的,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周杰伦的歌我没听过,但是我觉得流行歌曲入选教材没什么不可以——古代的诗词,我们现在奉为经典、国宝的东西,当初不过也是流行歌曲罢了——很大一部分还是经妓女传唱起来的。
什么歌曲算爱国歌曲啊?这不是扯淡吗?再好好想想,什么爱国,什么歌曲……
[em05]
世道注定要变的,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周杰伦的歌我没听过,但是我觉得流行歌曲入选教材没什么不可以——古代的诗词,我们现在奉为经典、国宝的东西,当初不过也是流行歌曲罢了——很大一部分还是经妓女传唱起来的。
什么歌曲算爱国歌曲啊?这不是扯淡吗?再好好想想,什么爱国,什么歌曲……
[em05]
| 欢迎光临 罗大佑音乐联盟网论坛 (http://www.luodayou.net/bbs2/) | Powered by Discuz! 6.0.0 |